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点击图片查看专题↑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一大类由自身免疫机制介导的脑炎。自2007年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脑炎被发现以来,目前已有二十余种相关自身抗体被报道。近几年,自身免疫性脑炎研究领域已经从发现自身抗体过渡到更精细认识不同类型脑炎的多维度特征乃至于尝试新的、特异性治疗方法的阶段。2024年自身免疫性脑炎研究领域依旧活跃热门,有不少重要研究发表。以下就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影像、发病机制及治疗靶点等方面盘点该领域2024年的研究进展。

抗NMDAR脑炎是最为常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然而,目前关于自体抗体如何识别和改变受体功能的认识仍然有限。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等多家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共同完成一项旨在于揭示抗NMDAR自身抗体(NMDAR-Ab)结合至NMDAR的抗原表位,并阐明患者来源的单克隆抗体导致NMDAR内吞的致病机制[1]。该研究首先分选出来自患者的单个B细胞,进一步克隆生产并鉴定出针对NMDAR的单克隆自身抗体。对两株代表性单克隆抗体Fab段与NMDAR复合物的冷冻电子显微镜分析发现自体抗体结合至NMDAR的GluN1亚基的氨基端结构域的不同抗原表位。两株单克隆抗体导致神经元表面NMDAR数量及其介导的活动减弱,却不会持续性影响NMDAR通道的门控功能。在另一项同期发表的背靠背研究中,来自美国、德国的多中心研究者同样克隆出人源单克隆抗NMDAR抗体并进行了结构解析及机制研究[2]。该研究解析了三株不同患者来源单克隆自身抗体结合至NMDAR的结构学特征。同样地,这些抗体结合在GluN1亚单位的氨基端结构域的不同区域,且结合的抗原表位不同于前述研究[1]。通过电生理学实验发现这三种单克隆抗体都可导致原代神经元中NMDAR通道的功能下降,其中一种抗体还导致突触上NMDAR数量的减少。
上述两项研究揭示了NMDAR-Ab在自身免疫性脑炎中多样的表位识别机制,打破了既往认为的自身抗体主要识别单一位点的观念。同时也提出了识别不同表位的自身抗体具有的致病性机制是否相同,其最终效应是否殊途同归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NMDAR-Ab具有致病性,但NMDAR-Ab的超早期致病机制尚不清楚。来自法国的一项研究使用单分子成像技术揭示了NMDAR-Ab对活体海马神经元的时空作用[3]。该研究发现NMDAR-Ab首先主要影响突触外,而非突触上的NMDAR。在最初数分钟内,NMDAR-Ab增加突触外NMDAR的膜动力学,还导致突触外区域的膜蛋白迅速重排。当持续暴露时,NMDAR-Ab通过非交联依赖的方式减缓受体膜动力学而减少NMDAR的突触池。该研究揭示了NMDAR-Ab最初损害突触外蛋白,随后才是突触蛋白,为NMDAR-Ab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该研究组还发现NMDAR的正向别构调节剂SGE-301在突触和突触外膜区都能拮抗自身抗体导致的受体膜动力学抑制[4]。提示SGE-301可能成为治疗抗NMDAR脑炎的一种潜在治疗策略。
既往研究发现识别NR1亚单位的NR1-IgGs在抗NMDAR脑炎中的致病性得到公认,但其产生的免疫生物学机制仍不清楚。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探索了NR1-IgGs的来源,并评估了不同B细胞亚群对血清中NR1-IgGs水平的贡献[5]。该研究从患者和健康对照获得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分选出初始B细胞、未转化记忆B细胞(USM)、已转化记忆B细胞(SM)、抗体分泌细胞(ASCs)及去除ASCs的PBMC,并在体外进行培养。研究结果发现部分抗NMDAR脑炎患者的PBMCs可自发产生NR1-IgGs。与PBMC阴性组的患者相比,阳性组脑脊液中的NR1-IgG滴度和mRS评分显著增高。PBMC培养中NR1-IgG阳性孔的比例与血清和脑脊液中的NR1-IgG滴度相关。与ASCs阴性组患者相比,阳性组在3个月随访时对二线免疫治疗反应较差。初始B细胞也能产生NR1-IgGs,这表明NR1-IgGs可能部分来源于初始B细胞。这些发现提示ASCs可能是NMDAR抗体脑炎患者急性期外周NR1-IgG的主要产生来源。该研究为开发靶向抗体分泌细胞治疗(如抗-CD38)提供了线索。
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利用抗LGI1和CASPR2抗体介导的两种常见自身免疫性脑炎作为人类模型描述了脑脊液B细胞受体(BCR)特征[6]。该研究从三名患者的脑脊液中,通过细胞分选和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分离出381对配对的IgG BCR,有166种以单克隆抗体形式表达。62%的单克隆抗体能够与LGI1或CASPR2反应。这些自身抗原反应性BCR主要集中在抗体分泌细胞中。携带具有LGI1和CASPR2反应性BCR的细胞更加分化。尽管具有更高的分化水平,反应性细胞在鞘内仅获得了少量突变,并且在克隆扩增过程中,抗原亲和力变化很小。该研究提示在抗LGI1和CASPR2脑炎患者中,抗原反应性BCR的成熟主要是在外周获得的。

抗NMDAR脑炎的长期结局仍不清楚,尽管80%-90%的抗NMDAR脑炎患者能够恢复独立生活,但大多数患者仍然面临持续的认知和社会心理障碍。且目前通常仅使用改良Rankin量表(mRS)作为报告的唯一结局,这可能无法充分反映真实的预后情况。本年度数个研究采用多项结局指标试图更精准描述抗NMDAR脑炎的长期预后。
来自荷兰的Brenner等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横断面和前瞻性队列研究[7],其研究对象为荷兰全国范围内的16岁以上抗NMDAR脑炎患者。该研究共纳入92名患者(年龄29 ± 2岁;77%为女性)。认知评分随评估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最多可达诊断后36个月,其中在前6个月的改善最为显著。在36个月之后,尽管大多数患者(91%)根据mRS量表显示为“良好”结果(≤2),但34%的患者表现出持续的认知障碍,65%的患者在1个或多个认知领域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是记忆和语言。患者自我报告的主诉方面发现情感、社交功能、精力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低于正常人群。许多患者未能恢复上学/工作(30%)或需要调整工作或学习(18%)才能适应。
另一项来自美国的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探讨了抗NMDAR脑炎成人患者的结局指标,包括mRS、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评估量表[CASE]、认知障碍(蒙特利尔认知评估/简易精神状态检查)、抑郁(患者健康问卷-9)和焦虑(广泛性焦虑障碍-7)及其相互的关联[8]。该研究共纳入38名患者(76%女性,中位发病年龄为28岁,范围为1-75岁)。长期随访(中位数=70周,IQR=51-174)中,患者的中位/均值mRS和CASE分别为2(IQR=1-3)和4.4(SD=4.2)。只有急性期肌力减退与远期较高的mRS评分相关。尽管患者远期mRS和CASE均较基线有所改善,但仅有31%的患者恢复到其发病前的功能状态。发病后超过6个月接受认知和情绪评估的患者中,中度至重度认知障碍(42%)、抑郁症(28%)和焦虑症(30%)较为常见。
第三项来自德国的横断面调查研究显示,抗NMDAR脑炎恢复期患者(随访时间中位数4.5年,范围0.3–30.3年)与常模人群相比,患者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显著增加。睡眠、运动和疲劳问题更为普遍。此外,患者自评记忆能力较低,使用的认知应对策略显著较少[9]。
上述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持续的神经精神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是抗NMDAR脑炎患者远期生活质量下降的原因。尽管大多数抗NMDAR脑炎患者的mRS随时间改善,但其并不能精确反映患者的后遗损害情况,无法捕捉情绪、认知等方面的长期功能损害的程度。因此需要更多利用更精细化的认知和情绪结局评估,同时也提出了如何以患者为中心制定恢复期疾病应对策略的重要问题。
此外还有一项研究关注了儿童抗NMDAR脑炎的远期预后[10]。该研究共纳入76名年龄不超过18岁的患儿,并进行最少5年的随访。其中有8名(11%)去世,68名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为7.1年(标准差1.5年,范围:5.0-10.1年)。恢复情况分为三类:完全恢复(50名;73%);行为和学校/工作功能缺陷(12名;18%);以及包括自理能力、行为认知障碍和癫痫的多领域缺陷(6名;9%)。发病年龄较小与多领域缺陷显著相关。这项研究同样提升大多数患儿在日常功能上有显著或完全的恢复,但大约五分之一的儿童仍然存在行为和学校/工作方面的缺陷。患者发病时年龄越小,残留多领域缺陷并依赖社会-家庭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一项来自西班牙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关注了另一种常见自身免疫性脑炎,即抗亮氨酸丰富的神经胶质瘤抑制蛋白1(LGI1)脑炎的预后[11]。该研究旨在描述抗LGI1脑炎患者接受初始免疫治疗后的1年内的临床特征。共纳入24名抗LGI1脑炎患者(平均年龄63岁[标准差12];13名[54%]为女性,11名[46%]为男性),在研究入组时、6个月和12个月接受神经精神评估和视频多导睡眠监测。18名(43%)健康成人(平均年龄62岁[标准差10];11名[61%]为女性,7名[39%]为男性)作为对照。入组时,视频多导睡眠监测显示19名(79%)患者的睡眠结构受损,而对照没有(p=0.013)。在第12月时,20名患者中的13名(65%)仍然有认知缺损。持续的认知缺损与入组前未使用利妥昔单抗、入组时快速眼动睡眠期无肌张力,以及入组时血清中存在LGI1抗体相关。该研究显示在初始免疫治疗后的第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抗LGI1脑炎患者常常出现未被察觉但持续存在的临床和视频多导睡眠监测变化。提示这些临床及功能学变化是可治的且可能会影响认知结果,同时也可以考虑作为临床试验中的结局指标。

一项基于2011-2022年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估算了按种族和族裔分层的年龄标准化和性别标准化抗NMDAR脑炎发病率[12]。该研究发现按年龄和性别标准化的抗NMDAR脑炎发病率(每百万人年)在黑人(2.94,95% CI 1.27-4.61)、西班牙裔(2.17,95% CI 1.51-2.83)和亚裔/太平洋岛屿人群(2.02,95% CI 0.77-3.28)中显著高于白人群体(0.40,95% CI 0.08-0.72)。在黑人女性中,卵巢畸胎瘤的发生率为58.3%,而在其他群体中为10%-28.6%。该研究提示抗NMDAR脑炎在黑人、西班牙裔或亚裔/太平洋岛屿人群中发生的比例较高。卵巢畸胎瘤在黑人女性中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诱发因素。导致上述族裔发病差异的环境和生物学风险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项来自西班牙的单中心研究纳入了2011-2022年期间怀疑为急性脑炎且排除ADEM的18岁以下儿童,并对这些患者的血清或脑脊液样本进行了系统性自身抗体检测[13]。在2750名儿童中,542名(20%)患儿的血清或脑脊液样本显示TBA阳性,且主要(>90%)针对神经细胞表面抗原。仅19名患儿的抗体TBA阴性,但CBA检测阳性。儿童脑炎患者中最常见的是针对NMDAR(76%)和MOG(5%)的抗体,其次是GAD65(2%)和γ-氨基丁酸A型受体(2%)。而针对其他已知细胞表面或细胞内神经抗原的抗体(占所有阳性病例的6%)以及对未知抗原的抗体(9%)非常少见。这些研究提示儿童急性脑炎患者的自身抗体谱与成人不同。除NMDAR和MOG抗体外,目前常用的抗体检测谱中包含的许多抗体很少阳性,因此在儿童中进行这些抗体的筛查的必要性值得商榷。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快速准确诊断有助于及时启动免疫治疗,从而改善患者预后。然而,单凭临床特征可能不足以缩小鉴别诊断范围,等待自体抗体结果又可能会延迟免疫治疗的开始。一项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医院和美国梅奥诊所的横断面研究关注了常规磁共振成像的特征是否能准确区分两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类型(抗LGI1和CASPR2脑炎)与两种主要的鉴别诊断疾病——病毒性脑炎(VE)和克雅二氏病(CJD)[14]。该研究纳入192名患者的首次可用头颅MRI进行回顾性盲法分析,诊断由两位神经影像学家进行评估(发现队列;n = 87);结果在独立队列中通过三位神经科医生验证(n = 105)。关注的MRI异常表现包括:T2和/或FLAIR高信号、肿胀或萎缩、是否钆增强、弥散加权成像变化以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与VE和CJD相比,抗LGI1和CASPR2脑炎T2和/或FLAIR高信号较少延伸至颞叶以外,肿胀的发生频率较低,未出现弥散受限,钆增强很少见。独立队列验证了上述发现。在海马和/或杏仁核存在T2/FLAIR高信号病例中上述特征组合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7,灵敏度为90%,特异性为95%。这一研究提示常规MRI的某些表现有助于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鉴别诊断和临床决策,促进免疫治疗的及时启动。但尚待后续研究验证其在其他类型自身免疫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鉴别中的价值。
血脑屏障(BBB)通透性变化可能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病理机制之一。一项来自韩国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通过动态对比增强(DCE)MRI评估了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BBB通透性变化,同时探索其对患者治疗反应的预测价值[15]。共有38名患者(中位年龄38岁[四分位差:29-59岁];20人[53%]为女性)和17名对照组(中位年龄71岁[四分位差:63-77岁];12人[71%]为女性)纳入该研究。与对照组相比,所有脑区的Ktrans值在患者中均显著升高,其中右侧海马旁回的差异最大。治疗反应差的患者小脑皮层、左大脑皮层和左后中央回的基线Ktrans值均高于治疗反应良好组。这一研究揭示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存在BBB通透性增加,且部分脑区基线Ktrans与治疗反应相关。
来自瑞金医院团队报道了在体可视化神经炎症中的小胶质细胞激活的(18)F-DPA-714 PET融合MRI在自身免疫性脑炎中的应用价值[16]。该研究共纳入25名患者(平均年龄39.24岁 ± 19.03)和10名健康对照(平均年龄28.70岁 ± 5.14)。这些患者的自身抗体各异,包括针对胶质细胞抗原MOG、GFAP,神经元表面抗原NMDAR、LGI1、GABABR、Caspr2等,胞内抗原SOX1、GAD等。研究发现(18)F-DPA-714 PET检测的阳性率为72%(18/25),而使用常规MRI的阳性率为44%(11/2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65)。发生癫痫的患者与未发生癫痫的患者相比,整个皮层区域的平均SUVR显著升高。在13名接受随访的患者中,11名(85%)在免疫抑制治疗后显示(18)F-DPA-714的摄取减少,并伴随症状缓解。
[1] Wang H, Xie C, Deng B,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antibody-mediated NMDA receptor clustering and endocytosis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Nat Struct Mol Biol, 2024.
[2] Michalski K, Abdulla T, Kleeman S, et 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anti-NMDA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Nat Struct Mol Biol, 2024.
[3] Jamet Z, Mergaux C, Meras M, et al. NMDA receptor autoantibodies primarily impair the extrasynaptic compartment[J]. Brain, 2024, 147(8): 2745-2760.
[4] Maudes E, Jamet Z, Marmolejo L, et al. Positive Allosteric Modulation of NMDARs Prevents the Altered Surface Dynamics Caused by Patients' Antibodies[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4, 11(4): e200261.
[5] Qing Li A, Jie Li X, Liu X, et al. Antibody-secreting cells as a source of NR1-IgGs in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antibody encephalitis[J]. Brain Behav Immun, 2024, 120: 181-186.
[6] Theorell J, Harrison R, Williams R, et al. Ultrahigh frequencies of peripherally matured LGI1- and CASPR2-reactive B cells characterize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24, 121(7): e2311049121.
[7] Brenner J, Ruhe C J, Kulderij I, et al. Long-Term Cognitive, Functional, and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nti-NMDAR Encephalitis[J]. Neurology, 2024, 103(12): e210109.
[8] Morgan A, Li Y, Thompson N R, et al. Longitudinal Disability,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od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J]. Neurology, 2024, 102(4): e208019.
[9] Heine J, Boeken O J, Rekers S, et al.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 in 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5, 12(1): e200343.
[10] Chen L W, Olivé-Cirera G, Fonseca E G, et al. Very 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Dependency in Children With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4, 11(3): e200235.
[11] Muñoz-Lopetegi A, Guasp M, Prades L, et al. Neurological, psychiatric, and sleep investigations after treatment of anti-leucine-rich glioma-inactivated protein 1 (LGI1) encephalitis in Spa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Lancet Neurol, 2024, 23(3): 256-266.
[12] Alsalek S, Schwarzmann K B, Budhathoki S, et al.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in the Incidence of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4, 11(4): e200255.
[13] Chen L W, Guasp M, Olivé-Cirera G, et al. Antibody Investigations in 2,750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4, 11(1).
[14] Kelly M J, Grant E, Murchison A G,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LGI1-Antibody and CASPR2-Antibody Encephalitis[J]. JAMA Neurol, 2024, 81(5): 525-533.
[15] Ji S H, Yoo R E, Choi S H, et al.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Quantification of Alter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Radiology, 2024, 310(3): e230701.
[16] Zhang M, Meng H, Zhou Q, et 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Imaging Using (18)F-DPA-714 PET/MRI for Detecting Autoimmune Encephalitis[J]. Radiology, 2024, 310(3): e230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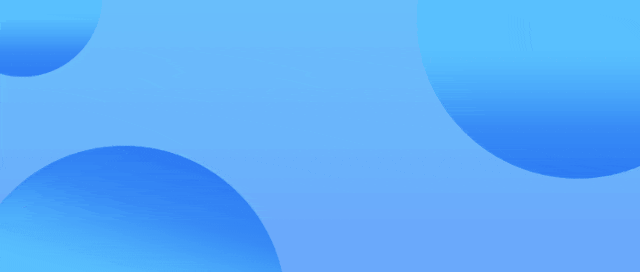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