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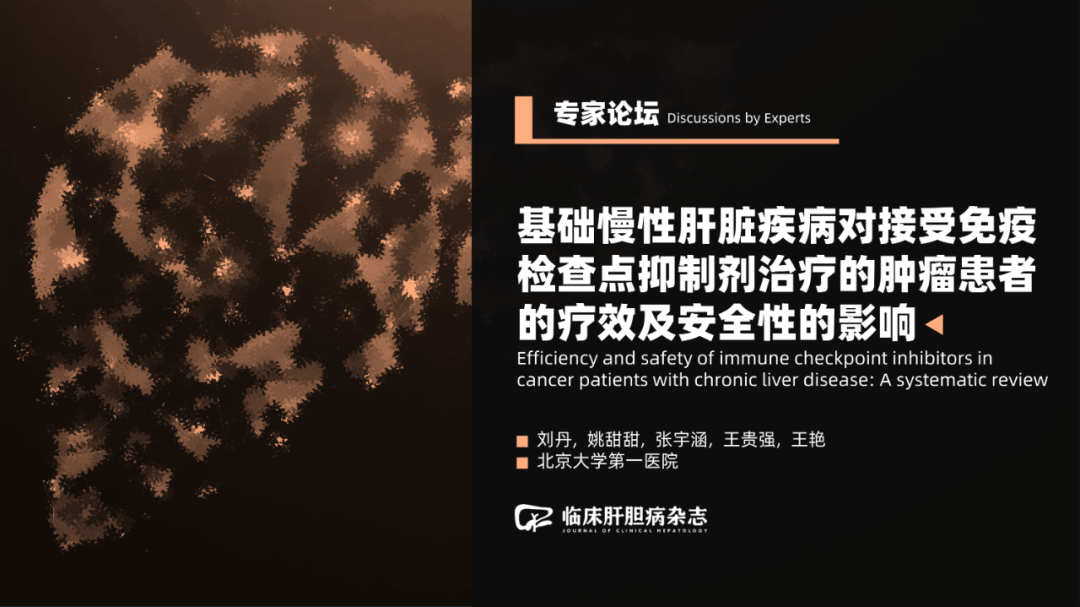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通过打破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目前已被批准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迄今为止,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肿瘤治疗的ICI共三种[1], 包括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抗体以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抗体,这些ICI均已证实对黑色素瘤、肾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头颈部肿瘤、霍奇金淋巴瘤、肝癌等多种肿瘤有效。随着ICI的广泛应用,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报告率逐渐增加,所累及的器官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皮肤、胃肠道、肝脏、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造血系统以及泌尿系统等[2]。
肝脏受累是irAE的突出表现之一[3],可发生于接受ICI治疗的不同时间点,表现为不同程度转氨酶升高,甚至肝衰竭。可能与应用ICI后免疫系统被非特异性激活有关,具体机制仍处于研究阶段。在我国,慢性乙型肝炎(CHB)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率高达6.52%、22.4%[4],因此伴有慢性肝脏疾病(CLD)基础的肿瘤患者较为常见。然而,基础CLD是否影响ICI的有效性,以及CLD患者应用ICI的安全性问题尚需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和进一步深入探究。针对此热点问题,本综述简要概述其相关的研究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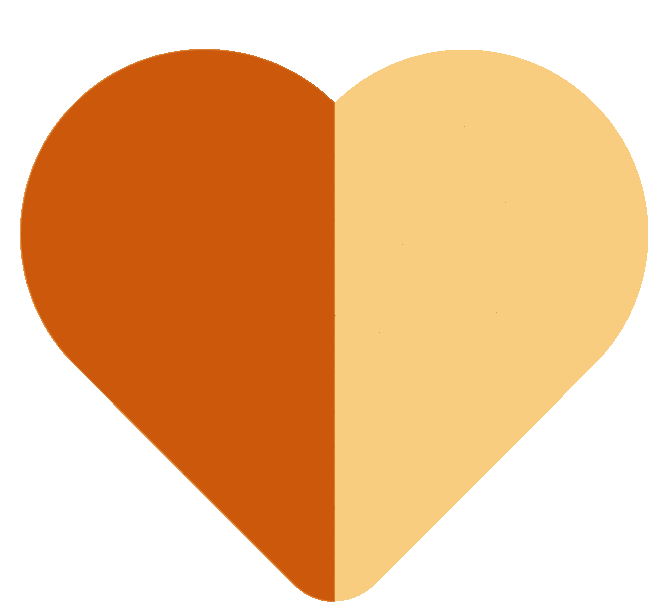
ICI已被批准用于晚期肝细胞癌(HCC)的治疗[5]。HBV和HCV感染是HCC最主要的病因[6]。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的HCC患者接受ICI免疫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备受关注。作为ICI被批准治疗肝癌的重要依据CheckMate-040研究[5]表明,纳武利尤单抗的客观缓解率(ORR)为20%。在该研究的亚洲患者亚组队列中[7],感染HBV/HCV的队列ORR、疾病控制率、6个月生存期、中位生存期、中位缓解持续时间等生存评价指标与不伴HBV/HCV感染的队列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另外一项系统评价研究[8]同样表明,伴HBV/HCV感染的HCC患者的ICI治疗有效率为18.6%,与CheckMate-040研究结论相似。我国48例HBV-HCC患者接受ICI治疗的ORR为31.3%,疾病控制率为66.7%[9]。因此,无论是否伴有HBV/HCV感染,ICI的有效性不受影响,HCC患者均可从ICI中获益。
在接受ICI治疗期间,部分病例会出现轻微、短暂的不良事件(AE),如转氨酶升高或irAE(如皮疹、结肠炎、肺炎、急性肝炎)等,其中irAE的发生机制可能与ICI引起机体免疫过度激活相关。新加坡一项纳入114例HCC患者(54%的HBV感染,11%的HCV感染)的真实世界研究[10]表明,AE发生率为69.3%,其中肝脏相关AE占21.9%,3级以上AE为14.9%。CheckMate-040研究[5]发现,19%的HCC患者在接受ICI治疗后出现3级以上irAE,4%的患者出现3级以上治疗相关严重AE。CheckMate-040研究[7]中病因为病毒性肝炎的HCC患者占比为51%,而其亚洲亚组队列中病因为病毒性肝炎的HCC患者比例更高(71%),且大多数irAE的严重程度为1/2级,很少需要免疫治疗,3级以上irAE的发生率为16%,与CheckMate-040研究总人群类似(19%)。并且肝脏相关的所有等级irAE和3级以上irAE的发生率分别为4%、1%,主要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一项纳入40例HCV感染的肿瘤患者(30%HCC)的研究[11]表明,3级以上irAE发生率为5%(2/40),其中有2例在应用ICI后出现转氨酶升高。在另一项纳入34例HBV/HCV感染的肿瘤患者(47%HCC)的队列[12]中,所有等级的irAE发生率为44%,其中≥ 3级irAE发生率为29%。我国的一项研究[9]表明,48例HBV-HCC患者中45.8%的患者至少经历过1次AE,25%发生3级以上irAE。因此,合并病毒性肝炎的HCC患者应用ICI治疗整体安全性好。
在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居首位,其中NSCLC约占肺癌总数的85%,近年来随着ICI抗肿瘤有效性数据的逐步夯实,丰富了NSCLC的现有临床治疗方案[13-14]。由于肺癌的高发病率,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的NSCLC人群不容忽视。而很多非肝癌的临床试验将合并HBV/HCV的人群排除在外,因此尚缺乏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的NSCLC人群大样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临床数据。从小样本的真实世界临床研究[8, 11]结果发现,合并HBV/HCV感染的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表现出稳定的客观肿瘤应答,病毒载量无明显变化,未出现病毒再激活,未发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病例。虽然部分病例出现irAE,但irAE发生率为35%~44%,其中3级以上irAE发生率为17%~29%,且均无需终止免疫治疗,在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后均好转[12, 15]。在一项纳入19例HBV/HCV-NSCLC的研究中,ICI治疗的ORR为3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5个月[16],均高于NSCLC的CheckMate-017和CheckMate-057研究[13-14],可能与该研究样本数量相对较少或该队列中PD-L1阴性病例的数量相对较少相关。因此未来需要更大的样本队列来明确HBV/HCV感染是否对ICI治疗NSCL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产生影响。
黑色素瘤是推动免疫治疗发展的最重要肿瘤,2011年FDA批准抗anti-CTLA-4治疗晚期黑色素瘤,标志着ICI时代的开始[17]。同样,在临床研究阶段病毒性肝炎患者被排除,因此ICI在合并病毒性肝炎的黑色素瘤患者中的相关数据有限。一项纳入5例HBV感染的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18]发现,合并HBV感染不影响ICI对于黑色素瘤的疗效,经过伊匹木单抗(Ipilimumab)治疗后只有2例患者出现转氨酶升高,肝损伤的发生率与使用伊匹木单抗治疗的普通人群相似。我国一项纳入23例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19]发现,11例既往HBV感染的患者(其中3例接受预防性的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在ICI治疗期间未观察到ICI导致的严重肝毒性。
肝炎病毒再激活是合并病毒性肝炎的肿瘤患者接受ICI治疗最受关注的安全性问题。免疫治疗对病毒复制和宿主免疫状态的影响尚不清楚,使得这类患者的治疗更加复杂。CheckMate-040研究的HBV-HCC患者在接受ICI治疗过程中均接受抗病毒治疗,未出现HBV再激活,也未发现抗-HBs血清转换;HCV-HCC患者应用ICI治疗后,可出现一过性HCV RNA下降,但难以维持超过24周的持续病毒学应答。采用核苷酸类似物和ICI共同治疗的HBV-HCC患者,即使基线时HBV DNA>100 IU/mL也不会导致乙型肝炎再激活[20]。而没有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的HCC患者应用ICI治疗HBV再激活风险高(OR=17.50,P=0.004)[21]。在一项纳入3465例肿瘤患者(15%的HBsAg阳性患者)接受ICI治疗的队列中,总患者、HBsAg阳性患者和HBsAg阴性患者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分别为0.14%、1.0%和0。其中HBsAg阳性的HCC患者的HBV再激活率为0.5%,在预防性抗病毒和无抗病毒HBsAg阳性患者中,HBV再激活率分别为0.4%(2/464)和6.4%(3/47)。这5例发生HBV再激活的患者中,有2例不规律进行抗病毒预防治疗(1例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差,1例自行终止治疗),另外3例未进行抗病毒预防治疗[22]。这也同样表明在ICI治疗HCC期间,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的HBV感染患者很少出现HBV再激活,而未进行有效的抗病毒预防治疗或接受治疗但依从性差的群体更易出现HBV再激活事件。一项最新的纳入13项研究2561例患者的综述研究[23]表明,HBV再激活的发生率分别为10.0%(未予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组)、1.0%(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组)和0(HBV既往感染者)。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合并HBV感染的肿瘤患者接受ICI治疗HBV再激活风险,无论基线血清HBV DNA如何,均应预防性抗病毒治疗。而既往感染过HBV的患者(抗HBc阳性、HBsAg阴性),HBV再激活罕见,可对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密切监测或按需抗病毒治疗。
综上,慢性病毒性肝炎不会影响ICI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患有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癌症患者不是接受ICI治疗的禁忌证。并建议对于HBV感染者,无论HBV DNA水平如何,在接受ICI治疗前均应积极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降低HBV再激活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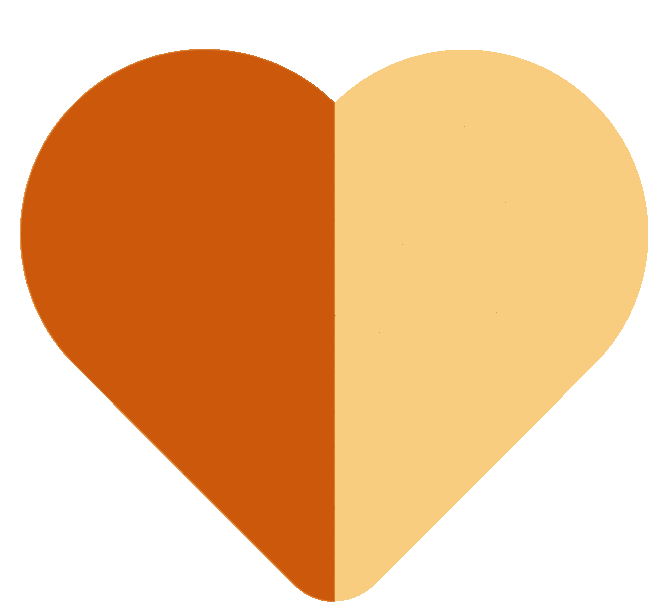
NAFLD发病率逐渐升高,相关HCC死亡人数每年增加1.4%,是目前全球HCC患者上升速度最快的病因[24],也是备受关注的慢性肝病,拟接受ICI治疗的合并NAFLD的肿瘤患者群体庞大,基于此对合并NAFLD的肿瘤患者ICI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综述。
NAFLD患者机体微环境适宜肿瘤生长,通过影响巨噬细胞极化和T淋巴细胞浸润调节免疫反应,可进一步加重肝脏微环境炎症反应,并导致肿瘤进展[25]。最近发表在Nature的一项纳入1656例晚期HCC患者的研究[26]表明,ICI不能提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相关HCC患者的生存率。在校正了与预后相关的混杂因素后(如肝损伤的严重程度、肝外转移、大血管的肿瘤侵袭程度等),NASH仍然是接受ICI治疗的HCC患者的生存期缩短的独立危险因素。该研究结果显示,NASH-HCC患者未能从ICI治疗中获益。原因可能是NASH患者的CD8+T淋巴细胞的免疫监测功能受损,导致NASH-HCC患者ICI治疗应答差,甚至会诱导NASH-HCC的发生[27]。同时,真实世界的研究[26]也同样发现,病因为NAFLD的HCC患者(11例,生存期8.8个月)接受ICI治疗的生存期低于其他病因的HCC患者(107例,生存期17.7个月)(P=0.034)。因上述两个队列研究中NAFLD-HCC患者数量较少,仍需要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安全性方面,上述研究未公开NAFLD-HCC患者ICI治疗的AE发生率。目前暂无NAFLD-HCC患者接受ICI治疗的安全性数据。可能原因是NAFLD并非HCC主要病因,因此这类患者人数较少。
虽然NAFLD-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临床是否获益尚有争议,但研究结果与NAFLD-HCC接受ICI治疗者大相径庭。与非NAFLD患者相比,NAFLD患者倾向有更高的BMI,高BMI的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可获得更高的抗肿瘤应答[27]。一项纳入2110例NSCLC患者(其中1434例接受ICI治疗)的研究[27]发现BMI≥30 kg/m2与ICI组患者的总生存率改善相关。另外一项纳入接受ICI治疗的635例NSCLC患者的研究[28]同样表明,肥胖的NSCL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和生存期显著延长。Wang等[29]通过临床研究验证了BMI≥30 kg/m2肥胖患者体内PD-1阳性T淋巴细胞增加,且T淋巴细胞增殖显著降低,但ICI治疗T淋巴细胞活化后可获得更佳疗效。继而设计了动物实验进一步明确机制。肥胖黑色素瘤小鼠与对照组相比,抑制性T淋巴细胞增加,T淋巴细胞功能降低、老化、耗竭。而给予ICI治疗后,通过打破免疫逃逸,激活T淋巴细胞功能,瘦素参与的相关信号通路的活化,使肥胖小鼠肿瘤模型获得更高抗肿瘤疗效、并获得更长生存期[29]。
但是也有一项纳入223例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研究[30]有不同的结论。该研究发现NAFLD组患者BMI更高,但在ORR、肿瘤控制率、无进展生存期等生存指标方面,NAFLD组与对照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即NAFLD-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无明显临床获益。然而在肝转移的亚组队列分析中,提示NAFLD与伴有肝转移的NSCLC患者预后改善相关,生存指标具有统计学差异。因此,NAFLD-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获益与BMI、是否存在肝转移相关,合并肝转移的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可能获益。
安全性相关研究结果目前也并不统一。既往研究[31]认为NAFLD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风险更高。一项探究ICI相关DILI风险因素的研究[32]结果证实NAFLD是PD-1抑制剂相关DILI的危险因素。此外,上文中提到的635例患者的研究[28]表明,高BMI的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发生irAE的比例更高(55.6% vs 25.2%,P<0.000 1)。但另有研究[27]表明接受ICI治疗的NSCLC患者BMI与irAE发生无关。以上均提示应重视NAFLD-NSCLC患者的ICI疗效及安全性观察,有无合并NAFLD或基线BMI应被视为ICI治疗NSCLC的重要分层因素。
目前尚未有NAFLD-黑色素瘤患者接受ICI治疗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研究。在黑色素瘤患者中,细胞质中的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 (MDA5)的激活会引起黑色素瘤细胞特异性凋亡,而MDA5是NASH的一个重要抑制因子,有可能解释黑色素瘤患者脂肪肝患病率不高[33]。但有研究[34]表明,超重(BMI≥25 kg/m2)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接受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男性患者相较于接受化疗者,可获得更高的无进展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而两组之间irAE的发生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超重组生存率的提高并不能用低irAE发生率可能提高治疗耐受性来解释。另外一项纳入接受ICI治疗的183例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28]验证了高BMI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生存期显著延长,但同时irAE发生率更高(55.6% vs 25.2%,P<0.00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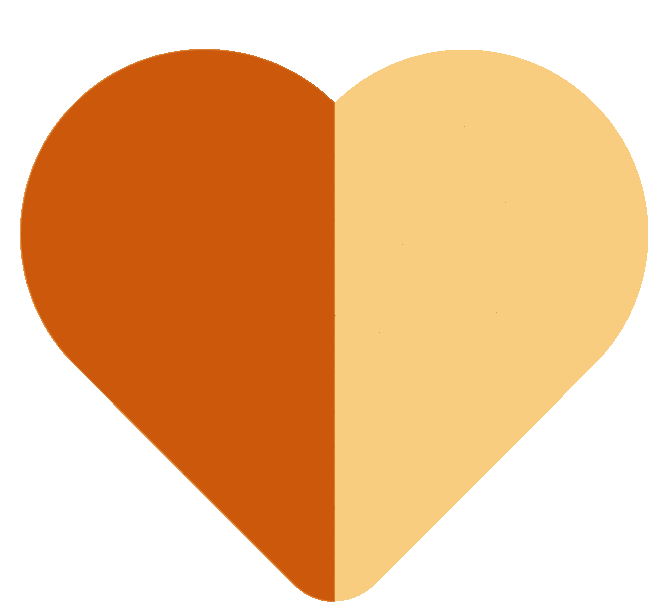
目前有相关文献[35-36]报道既往合并自身免疫疾病的癌症患者可安全使用ICI,但其中与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的病例几乎没有报道。2020年,Bhave等[37]报道了1例确诊为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重叠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重叠综合征患者,因Ⅲ期黑色素瘤转移使用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治疗,治疗4个周期评估有效性良好,并且无肝炎及其他不良事件发生。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PBC、AIH等存在自身免疫性肝病基础的肿瘤患者是否影响ICI的疗效和安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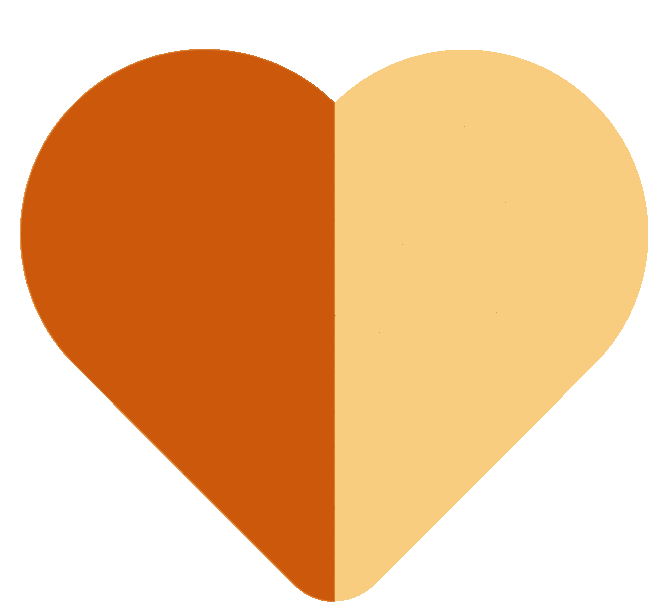
晚期HCC的预后不仅取决于肿瘤负荷,还取决于肝脏的储备能力。但目前大部分关于ICI的临床研究纳入的均是Child-Pugh A级患者。CheckMate-040是第一个纳入肝功能为Child-Pugh B级HCC患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38]。研究结果显示,纳武利尤单抗治疗Child-Pugh B级的HCC患者肿瘤应答好(ORR为12.2%)、生存期(7.6个月)较索拉非尼治疗的Child-Pugh B级HCC患者的生存期(3~5个月)长,并且Child-Pugh B级队列接受ICI治疗的安全性与Child-Pugh A级队列相似,3级以上AE发生率分别为24%(Child-Pugh B级)和23%(Child-Pugh A级),irAE发生率也没有显著性差异。另有研究表明,相较于Child-Pugh B级HCC患者,Child-Pugh A级、AFP基线≥10 ng/mL伴AFP在4周内下降幅度超过10%的患者应用ICI可获得更高的ORR。因此,Child-Pugh分级是HCC患者ICI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39]。合并肝硬化的HCC或其他肿瘤患者接受ICI治疗的临床获益和安全性目前尚缺乏临床数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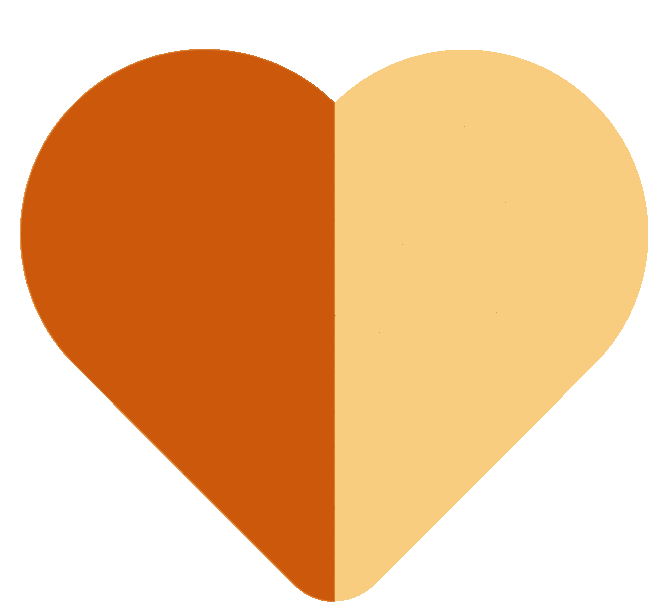
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拟接受ICI治疗的合并慢性肝病的肿瘤患者群体越来越大,但既往大多临床研究将基础肝病患者排除在外,因此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NAFLD、自身免疫性肝病及肝硬化等慢性基础肝病是否影响ICI的疗效以及安全性值得关注和探讨。肿瘤科医生和肝病科医生需要更紧密的多学科协作,推动前瞻性真实世界研究的开展,丰富循证医学证据,探讨慢性肝病患者免疫状态以及微环境的变化对肿瘤免疫治疗的影响和具体机制,为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临床和理论基础。
刘丹, 姚甜甜, 张宇涵, 等. 基础慢性肝脏疾病对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2, 38(11): 2457-2461.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