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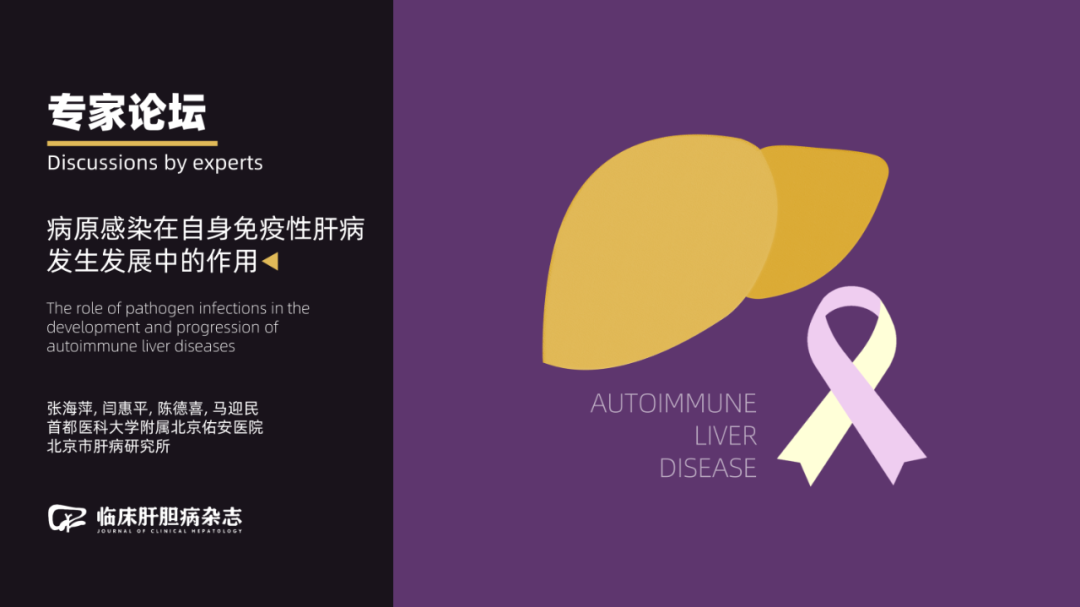
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主要包括以肝脏实质细胞炎症损伤为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以慢性肝内胆汁淤积为特征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和以特发性肝内外胆管炎症和纤维化为特征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与其他自身免疫疾病相似,这类免疫介导的肝胆疾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近年很多学者从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肠道微生态、分子模拟、化学药物、环境因素等各个方面陆续阐述了AILD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1]。但是,疾病是如何起始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依然知之甚少。
病原体感染与AILD发病相关的问题近年已有报道,包括感染肝炎病毒后出现AIH、或在明确HBV或HCV感染的患者中存在高滴度自身抗体和AILD的疾病特征,非常需要临床医生进行鉴别诊断。而且文献[2]证实,以大肠杆菌感染为主的尿路感染是PBC(尤其是女性患者)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EB病毒(EBV)、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等也有与自身免疫疾病的触发有关的报道。但是,这些病毒或细菌是如何造成机体免疫耐受机制被破坏,进而诱导出现AILD?下文将从分子模拟机制等方面简单介绍病原感染在AIH和PBC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1 分子模拟机制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学者[3]观察到寄生虫和宿主之间存在抗原交叉反应,并提出了保护性分子模拟的概念。此后,Damian将这种分子模拟的概念转移到了自身免疫领域,他认为病原体和宿主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或相互作用可能导致自身免疫[4]。近一步研究认识到,某些外来抗原与宿主细胞或细胞外抗原成份有序列同源性,进入人体后激发的免疫应答既攻击外来物质,也同时攻击人体的细胞或细胞外成份,因而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
分子模拟可能是外来抗原(传染源、药物、外来化学物质和肠道源性细菌等)打破机体自我耐受的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适应性免疫反应可以对与自身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表位致敏。产生分子模拟的物质与机体的自身抗原在结构或构象上有相似之处,入侵的病原体、自然环境中的抗原[5]、合成肽(化学制剂、氟烷)和疫苗[6]等都有可能是诱导交叉反应抗体和免疫细胞反应来打破自我耐受的外源性触发因素。在感染源与自身免疫的关系方面,已经证明多种细菌和病毒感染通过分子模拟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联,例如在格林-巴利综合征(GBS)中,已发现空肠弯曲菌感染与周围神经神经节苷脂结构(GM1)有同源性,而且GBS患者携带对低聚脂糖和GM1神经节苷脂都有反应的自身抗体(交叉抗体)[7-8]。另一个例子是化脓性链球菌M蛋白和人心肌肌球蛋白之间的分子模拟,风湿性心脏病相关瓣膜炎患者产生抗体和T淋巴细胞,这些抗体和T淋巴细胞对链球菌M蛋白和心肌肌球蛋白都有反应,而链球菌M蛋白免疫的大鼠也会发生瓣膜炎[9]。在肝病中,大肠杆菌等微生物通过分子模拟在PBC的病因中发挥作用,以下将有详细阐述。更新的例子见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有研究提示SARS-CoV-2可能是一种快速自身免疫和/或自身炎症失调的“激发因子”,在有遗传倾向的个体感染新冠病毒后,导致严重的间质性肺炎出现。2020年4月Zhang等报道[10],在某医疗队收治的我国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中,约40%出现抗磷脂抗体阳性(分子模拟机制可能参与其中),其他自身抗体阳性则少见。其中部分抗磷脂抗体阳性的患者出现脑梗塞等严重血栓事件,提示新冠肺炎患者体内存在自身免疫紊乱现象。
2病毒感染与AIH的发病
抗-LKM(含抗-LKM-1)是AIH-2型的标志性自身抗体,其靶抗原为细胞色素P450 2D6(CYP2D6)。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CYP2D6的免疫应答及抗原表位的各种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11]。AIH一般分为两型:AIH-1型以成人为主,占大多数,AIH-2型主要见于儿童和青少年,仅占AIH的4%~5%[12]。由此决定了临床上抗-LKM阳性病例十分少见。不仅少见,几项独立研究[13-15]表明,高达10%的HCV感染者中存在抗-LKM。笔者团队[16]对约10万例次肝功能异常患者检测自身抗体,仅发现抗LKM(或抗LKM-1)阳性15例, 其中符合AIH-2型诊断的患者7例,均为青少年;余8例诊断为丙型肝炎,均为中年以上患者。
为什么出现这种抗体交叉反应的现象?文献[17]报道,一些丙型肝炎患者在产生针对HCV蛋白NS3和NS5a的抗HCV抗体的同时还与CYP2D6蛋白的跨膜氨基酸254-288位的构象表位发生交叉反应。CYP2D6的这一区域包含免疫显性表位aa263-270。因此,HCV蛋白和CYP2D6蛋白某些区域之间的分子模拟可能是慢性HCV感染者出现这种交叉反应性自身抗体的一种解释。另一项针对60例LKM-1阳性和120例LKM-1阴性丙型肝炎患者的研究[18]观察到,LKM-1阳性患者存在AIH的表现,丙种球蛋白水平较高,肝内CD8 T淋巴细胞频率较高,而两组的抗病毒治疗效果相同。这表明,至少有一部分感染HCV的患者可能同时存在AIH。不过,鉴于国际自身免疫性肝炎组织(IAIHG)制定的诊断评分系统及简化评分系统都将病毒指标阳性作为减分标志物,因此,伴有抗-LKM阳性的HCV患者能否确诊AIH,对医生来说存在挑战。而且,困惑的问题还表现在二者有无因果关系?首先是仅存在交叉反应性抗体并不能证明HCV就是导致AIH的触发因素;其次,即使其中一些患者确实同时患有丙型肝炎和AIH,也难以确定HCV感染是AIH的启动因子。
HCV患者存在不同的自身抗体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现象。有报道[19]称,HCV多蛋白区域与三种平滑肌蛋白(波形蛋白、smoothelin、肌球蛋白)和两种核抗原(基质蛋白、组蛋白H2A)区域之间存在氨基酸序列的分子模拟。因而推测,HCV感染者的血清也可能是通过产生ASMA或ANA对上述一些模拟宿主抗原发生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初,甲型肝炎病毒感染和AIH的关系在58例AIH患者一级亲属队列中得到认识。3名亲属表现为亚临床甲型肝炎,而在此后的5个月内,3人中有2人发展成为AIH[20]。
不同类型的HBV感染者检测到自身抗体也是临床常见的情况,大部分自身抗体为低滴度非特异性的自身抗体,而且可能在疾病进程中减弱或消失。有研究[21]发现,数据库显示HBV蛋白与ANA/ASMA抗原靶位有区域同源性,例如,HBV DNA聚合酶与ANA中某些抗原成份:细胞核核心蛋白(NCP)、细胞核有丝分裂器(NUMA)、多发性硬化抗原(PM-Scl)等各有6~9个氨基酸序列同源,26%~40%的HBV感染者可能表现针对这些抗原的双倍活性。而在非病毒导致的肝病中缺乏这种反应性。
另一个有趣的病原体是EBV,多篇报道[22-23]认为其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1型糖尿病、干燥综合征和重症肌无力,以及AIH。有病例报告[24]描述了EBV感染后出现AIH:1例26个月大的女婴在最近的EBV感染后表现出AIH的典型特征,包括血清转氨酶水平升高、抗-LKM-1抗体的产生以及T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的界面性肝炎。虽然有记载的案例认为AIH的诊断与EBV感染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但是,由于EBV在人群中极高的感染率和AIH低的流行率,列举足够可靠的证据证明两者的因果关系还是极为困难的。
除了与HCV相关之外,人们还发现抗-LKM阳性AIH-2型患者识别的免疫优势表位aa254-271的序列含有一个核心序列PAQPPR,该序列也存在于人类α疱疹病毒1型(HHV-1)的感染细胞蛋白4(ICP4)中,从分子模拟机制表明,HHV-1感染也可能在AIH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25]。还有个案报道[26]认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会引发AIH:1例52岁的HIV感染者表现血清转氨酶和γ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ANA阳性以及伴有浆细胞增多的界面性肝炎。与以上病例不同的是,HIV感染和AIH的诊断在时间上不接近,相隔了7年;患者血清HAV、HCV、EBV和巨细胞病毒相关抗体呈阴性,但有既往HBV感染病史。因此这个病例或许是一个多种病毒感染在自身免疫紊乱条件下导致事实上自身免疫病发生的例子。此外HIV感染者的免疫状态受损可能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HIV感染期间CD4 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以及抗HIV治疗可能对调节性T淋巴细胞产生选择性影响,从而可能促进自身免疫疾病的发展。
3细菌感染与PBC的发生
PBC的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研究和大样本实验研究[27]表明,细菌感染特别是大肠杆菌感染通过分子模拟机制作用机体,是破坏线粒体自身抗原免疫耐受的一个关键因素,导致针对线粒体自身抗原的抗线粒体抗体(AMA)产生。
PBC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尿路感染问题首次报道于1984年,Burroughs描述了87例PBC患者中17例(19%)、89例其他慢性肝病患者中6例(7%)出现明显菌尿[28]。大肠杆菌通常是尿路感染中被分离到的主要微生物。但此后观察的结果并非一致,Floreani等[29]报道,PBC的尿路感染总患病率为11.2%,其他慢性肝病为12.1%(其中女性患者为18.4%),未能证明尿路感染在PBC患者中有显著差异。
进入21世纪后,几个欧美国家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病例对照研究[30-32]。Howel等在英格兰东北部进行的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100例PBC患者和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61%(58/100)的PBC和51%(109/223)的对照组未发生尿路感染,未能证明尿路感染与PBC的发生有关。此后他们在同一地理区域再次进行了大样本病例对照研究(n=318),此次的数据显示出PBC与尿路感染有显著关联[33]。他们将这两项研究的差异归因于前一项研究的小样本量及存在大量风险因素。一项在法国的研究[34]从2006年—2007年共纳入222例PBC患者。结果表明,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218例中104例(48%)和509例对照组中157例(31%)的尿路感染及复发史均与PBC显著相关(P=0.001)。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包括1032例PBC患者和年龄、性别、种族和地理位置的匹配的1041例对照组,再次确认了大肠杆菌为主的尿路感染史是PBC发病的显著危险因素。
在90%~95%的PBC患者中可以检测到AMA,它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物。AMA识别线粒体内膜中的一个酶家族,即2-氧乙酸脱氢酶复合物(2-OADC),主要包括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E2亚单位(PDC-E2),支链2-氧酸脱氢酶复合物(BCOADC-E2),2-氧戊二酸脱氢酶复合物(OGDC-E2)及二氢脂酰胺脱氢酶结合蛋白等(E3BP)。序列分析表明,人PDC-E2与大肠杆菌PDC-E2具有显著的同源性,特别是在AMA的免疫优势表位区域(表 1)。整个ExDK序列被人类和大肠杆菌PDC-E2共享,也是人类PDC-E2识别CD4+ PDC-E2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基本序列,这种人PDC-E2与大肠杆菌PDC-E2之间的分子模拟可能解释了线粒体自身抗原耐受性的破坏和AMA的产生。PDC-E2位于线粒体膜内,含有硫辛酸-赖氨酸键,这是抗原识别和免疫细胞激活所必需的。凋亡胆管上皮细胞(BEC)内PDC-E2异常修饰,使得在特征性的凋亡小泡内抗原表位保持免疫完整性。这种免疫原性复合物被循环中的AMA识别,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介导了靶向性胆道损伤。AMA对PBC的高度特异性提示它不仅是诊断PBC的血清学标志物,而且在PBC的免疫病理学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表1 人PDC-E2 155-1851*的分子模拟和免疫优势表位
人类PDC-E2 | KVGEKLSEGDLLAEIETDK*ATIGFEVQEEGY |
B淋巴细胞 | KVGEKLSEGDLLAEIETDK*ATIGFEVQEEGY |
CD4+T淋巴细胞 | KVGEKLSEGDLLAEIETDK*ATIGFEVQEEGY |
CD8+T淋巴细胞 | KVGEKLSEGDLLAEIETDK*ATIGFEVQEEGY |
E. coli PDC-E2 2** | K-G-----L-EIETDK-----G- |
Novosphingobium aromaticivorans | -----GD-LAEIETDKAT--FE---EG- |
PDC-E2 | |
注: *K为硫辛酸的附着位点173lysine(赖氮酸);横线部分为每种细胞识别的表位;* * ExDK序列存在于人源和大肠杆菌PDC-E2中。 | |
细胞免疫的研究[35]同时表明,大肠杆菌的感染可能导致自身反应性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识别自身抗原,致使对线粒体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被打破。PBC的组织学特征包括在门静脉周围近中小胆管的单个核细胞密集浸润,免疫组化对这些淋巴细胞的检测显示出优势CD4+和CD8+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PBC患者肝脏中的胆管上皮细胞和肝细胞也表达大量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Ⅰ类和Ⅱ类分子[36]。因此,CD4+和CD8+自身反应性T淋巴细胞在PBC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在PDC-E2上定位T淋巴细胞自身表位是一项重要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PBC的自身反应性细胞免疫提供了条件。首先,用重组PDC-E2多肽的重叠肽技术证明了PBC的肝内浸润性T淋巴细胞亚群是专门针对PDC-E2的[37]。此外,在PDC-E2的内脂酰结构域内的163-176氨基酸残基(GDLLAEITDKATI)被确定为最小T淋巴细胞表位(表 1),该表位由横跨整个PDC-E2序列的33个重叠合成肽组成。此外,这些CD4+T淋巴细胞克隆也识别其他线粒体抗原,包括OGDC-E2、BCOADC-E2和E3BP。
总之,已经证明PBC患者的血清可与人PDC-E2和大肠杆菌PDC-E2均发生反应,实验研究证实大肠杆菌感染通过分子模拟机制不仅在B淋巴细胞水平,也在T淋巴细胞水平可以引发免疫系统的对人PDC-E2耐受性的破坏。
大肠杆菌并不是破坏线粒体自身抗原耐受性的唯一细菌,在众多的候选菌中,新鞘氨醇杆菌属芳香新鞘氨醇菌(N. aromaticivorans)引起关注。该菌是一种革兰阴性需氧菌,其PDC-E2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人类PDC-E2的主要免疫原性脂酰化结构域也具有高度同源性(表 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微生物在环境中(土壤、水和沿海平原沉积物)无处不在[38]。可见,其他细菌也有可能通过分子模拟参与PBC的病因学[39],这给认识PBC的发病因素又增加了复杂性。
4 未解的问题
多年的研究表明,病原体与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起病有关,但是难以获取其在自身免疫破坏过程的启动和/或传播中发挥作用的直接确凿证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是所有病例都有特定病原体感染史,也不是所有受到该病原感染的人都发生了相关的自身免疫疾病。第二,某些患者既往可能确实遭遇某种病原体,但在自身免疫疾病诊断时,由于病原体消除又无明显的抗体而不能得到既往病原体感染的证据。第三,旁观者诱导的炎症使阻止肠道共生菌发生逃逸的屏障被破坏,可能发生微生物易位。研究者[40]发现一种肠道细菌——鹑鸡肠球菌(Enterococcus gallinarum)会迁移到肝脏、肠系膜等组织器官,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原位杂交方法确证自身免疫病遗传模型小鼠的肝脏中存在这种肠球菌;AIH患者的肝组织中也存在鹑鸡肠球菌,而正常人及非AIH患者肝脏组织则未发现这种细菌。第四,有人推测病原体感染到机体发生自身免疫损伤是一个漫长过程[23]。首次感染引起机体免疫反应以消灭入侵的生物体,病原体可能在几天或几周内被消灭,也可能持续存在较长时间。在慢性感染的情况下,免疫反应不足以完全消除病原,但由于病原体和宿主之间存在相似结构,最初针对该病原体产生的交叉反应性B淋巴细胞/抗体和/或T淋巴细胞会慢慢攻击宿主的类似结构,从而在该病原体感染后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导致自身免疫病发生。
综上所述,AILD的启动因素是复杂的,日常生活中、环境中的多种微生物、抗原物质均可能是自身免疫的诱发或启动因素。在病因与发病机制方面,有许多未知问题需要深入认识与探索。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研究成果,帮助认识病原体感染与AILD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管控和减少疾病的发生。
点击以下链接,免费下载PDF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