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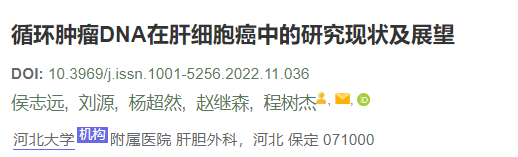
原发性肝癌被认为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诊断的癌症,也是全球第三大癌症死亡原因,肝癌在全球发病率中排名第五,其中肝细胞癌(HCC)占75%~85%[1]。中国是肝癌的发病大国之一,据统计,全世界肝癌患者中55%来自中国[2]。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慢性HBV或HCV感染、黄曲霉毒素B1暴露、饮酒和代谢综合征[3]。目前HCC的全球负担仍在增加,可能很快超过每年100万例的发病率[4]。尽管临床治疗(如切除)取得了进步,但由于复发和转移,晚期肝癌患者的预后并不理想,因此,术前早期诊断、术后恰当的辅助治疗成为延长患者生存期的重要方法,但由于缺乏可靠的诊断手段和有效的治疗方法,肝癌的死亡率在我国仍排在第2位[5],故需要迫切寻找更敏感、更具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目前,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通常使用影像学检查作为常规的临床监测方法,虽然包括CT、MRI或超声造影在内的成像技术已将灵敏度从66%提高到82%,特异度提高到90%以上,但仅仅是用于检测直径至少为1 cm的结节[6],而对直径<1 cm的极早期或不典型肝癌,使用液体活检技术则更有助于诊断及制订治疗方案。
液体活检的新诊断概念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7]。液体活检技术收集人体非固体生物组织的样本(如血液)用于不同的分析,其他的体液也可用于特殊的液体活检,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脑脊液、用于头颈部肿瘤的唾液、用于胸腔及转移性肿瘤的胸水、用于腹部及转移性肿瘤的腹水、用于胃肠道肿瘤的粪便和用于尿道癌的尿液[8]。液体活检由循环肿瘤细胞、细胞游离核酸[如循环肿瘤DNA(ctDNA)]、外泌体或肿瘤诱导的血小板等不同的生物基质组成。
游离DNA(cell-free DNA, cfDNA)是Mandel和Metais在1948年首次报道的在血液非细胞成分中发现的片段化DNA[9]。cfDNA通常为150~200个碱基对大小的双链DNA片段,其主要通过细胞凋亡或坏死释放到血流中。来自正常细胞的cfDNA在血浆中含量较低(平均为10~15 ng/mL)[10],并且在一些生理或者病理情况下(如运动、炎症、糖尿病、败血症、心肌梗塞及孕妇),cfDNA的水平会增加[11]。据观察,癌症患者中的cfDNA总体水平高于未患癌症的人[10]。ctDNA是特异性来源于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的cfDNA的一部分,尽管ctDNA在cfDNA中具有<0.1%~>90%的波动比例[8],但因其具有短半衰期、高敏感性、微创性、携带肿瘤的遗传信息等特点,可对其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从而确定其在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和进展监测方面的重要临床价值[12]。事实上,ctDNA的潜在价值在包括肝癌在内的各种癌症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cfDNA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8, 14],通过检测血浆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突变情况来指导靶向药物的应用,还可用于检测EGFR靶向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癌症进展患者的T790M EGFR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治疗耐药,从而指导更换靶向药物为第三代EGFR抑制剂(如奥希替尼)。同时,FDA也批准了cfDNA在结直肠癌中的应用[14],通过检测血浆中SEPT9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来指导药物对结直肠癌的应用,且已证实cfDNA高甲基化状态与结直肠癌的发生有关。
随着监管机构批准了多种新药,晚期HCC的临床管理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15]。一线和二线的治疗分配不是基于肿瘤特征,因为除了甲胎蛋白和雷莫芦单抗以外,没有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对任何特定治疗的反应[16]。von Felden等[17]为了能够分析基因的突变情况并确定对全身治疗反应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研究了121例晚期HCC患者的突变情况,结果发现具有PI3K/MTOR通路中DNA突变的患者在接受索拉非尼治疗后的无进展生存期明显短于没有突变的患者,说明PI3K/MTOR通路是索拉非尼耐药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研究结果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验证,但也证明了ctDNA分析的临床实用性及其对未来HCC生物标志物开发的重要性。
如今,移植肿瘤学在治疗肝胆恶性肿瘤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由于术后复发和移植后排斥,使得移植肿瘤学的发展受到阻碍。cfDNA已经成为器官移植患者管理的重要工具,cfDNA技术的进步为进行微小残留病灶(MRD)的移植前评估、移植排斥和癌症复发的移植后评估提供了选择[18]。Ng等[19]连续2年进行试验,结果表明GcfDNA片段的大小谱是评估肝移植后移植物损伤和排斥反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大多数HCC在早期是无症状的,而往往都是在后期被发现。目前,AFP是使用最广泛的HCC肿瘤标志物,但其缺乏敏感度(39%~65%)和特异度(76%~94%)[3],在早期肝癌中无法被检测到,甚至还会出现假阴性结果[20]。Chen等[21]分析了10项研究,他们评估了ctDNA与AFP联合检测的方法,发现ctDNA和AFP的联合检测比单独检测AFP能更准确地识别肝癌患者,并且相比于影像学检测,ctDNA检测能更早的识别出疾病复发或进展的患者。
尽管HCC中没有明确的致癌基因[1],但研究[22]已经验证了检测ctDNA中与HCC相关的体细胞突变以筛查早期患者的可行性。Wang等[13]检测到ctDNA中存在非常普遍的基因改变,如TP53、CTNNB1、AXIN1和TERT启动子,并且这项检测在包含331例患者的验证队列中表现出100%的敏感度和94%的特异度。研究[13]表明,基因启动子的高甲基化已被证明是HCC发生的早期事件。DNA甲基化可导致染色质结构、DNA构象、DNA稳定性以及DNA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发生变化,从而控制基因表达。Mohamed等[23]的实验结果表明,血清RASSF1A的甲基化水平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HCC,尤其是在HCV感染的高危患者中。另外,即使HCC患者在相似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系统(BCLC)阶段,不同的个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因此对靶向治疗的反应不同[24]。故而,在诊断时对自身肿瘤分子特征进行分类识别对于了解肿瘤的生物学背景、指导患者分层、提高治疗效果、预测预后至关重要[22]。
早期研究[25]表明,血浆中cfDNA水平与肿瘤负荷显著相关,因其具有高度特异性和短的半衰期,使得cfDNA具有预后价值的独特优势。有证据[26]表明,cfDNA突变可能与血管侵袭密切相关,且cfDNA突变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更短。García-Fernández等[27]发现,cfDNA中突变的P53基因可能被用作HCC患者肝移植后肿瘤复发的生物标志物。此外,因其较短的半衰期,cfDNA对治疗后肿瘤负荷的变化可以做出快速反应,因此可以通过检测肿瘤特异性分子的改变情况来改善预后。还有研究[28]表明,HCC患者手术后cfDNA水平显著下降,表明动态监测cfDNA水平的变化可以为术后残留病变和早期复发提供实时信息。
最近,对155例接受手术切除的HCC患者的一项研究[29]表明,cfDNA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的启动子甲基化与较差的总生存期和早期肿瘤复发存在显著联系。也有报道称,ctDNA中的异常甲基化可识别AFP阴性的HCC患者[30],并且异常甲基化与转移或复发风险增加[31]、更大的肿瘤[32]和更差的预后[30, 32]相关。总体而言,ctDNA的浓度、突变和甲基化模式等变化可以为检测残留病变、识别早期复发和预测HCC预后提供参考。
cfDNA应用于个体化治疗的肿瘤基因谱鉴定,这已成为癌症医学的基本实践[33]。近年来,免疫疗法已经成为HCC患者治疗所选择的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34]。TKI一直是局部晚期HCC患者的标准全身治疗选择,一线药物如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二线药物如瑞戈非尼、卡博替尼和雷莫芦单抗为晚期HCC的序贯全身治疗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只有不到40%的HCC患者才有资格接受免疫治疗[35],咎其原因可能是复杂和异质的突变环境。使用ctDNA对HCC中的突变进行量化已被证明是对免疫治疗和TKI反应的非常好的预测指标。因此,迫切需要评估和开发ctDNA的用途,以检查其是否可以成为评估免疫疗法或TKI反应的有效工具。研究[36]表明,TP53基因组的改变与VEGF-A表达增加相关,此类肿瘤可能成为贝伐珠单抗等抗血管生成药物的靶点。同时,一项针对于TP53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37]表明,采用含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更长于不含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另一项前瞻性研究[17]表明,PI3K/MTOR通路突变的患者在使用TKI后的无进展生存期明显短于没有这些突变的患者,但不是在免疫检查点抑制之后,说明ctDNA可作为对全身治疗原发性耐药的预测因子。
ctDNA检测除了指导分子靶向治疗以外,还可能有助于监测治疗反应,因为血浆中的突变状态已被证明可以反映患者的肿瘤负荷并与患者的临床状态有关[38]。到目前为止,尚未检测到相同的基因组谱,这表明分析患者的突变基因组景观可以实现有针对的特异性治疗。例如,Ikeda等[39]评估了14例患者,结果表明具有PTEN失活和MET激活突变的晚期HCC患者可以从西罗莫司和卡博替尼的治疗中受益,具有CDKN2A失活和CTNNB1激活突变的患者在接受帕博西尼和塞来昔布联合治疗后,AFP水平降低。其次,ctDNA还可以作为评估瑞美替尼单药治疗和瑞美替尼与索拉非尼联合治疗在具有突变RAS等位基因的晚期HCC患者中的治疗效率的合格工具[40]。此外,Galle等[41]研究证明,上皮- 间质转化(EMT)驱动的DNA甲基化是晚期HCC患者对索拉非尼耐药性的基础。因此,通过监测EMT过程中ctDNA的甲基化变化,可以预测肿瘤反应及耐药机制。
以免疫检查点阻断(ICB)为代表的免疫疗法已经改变了癌症治疗的临床实践。目前,对于血清AFP水平≥400 ng/mL的晚期HCC患者,推荐雷莫芦单抗作为索拉非尼之后的二线药物[16]。尽管ICB全身治疗取得了初步成功,但需要使用分子检测来确定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ctDNA可以区分真正的肿瘤进展和由ICB治疗造成的炎症引起的假进展[15],并且ctDNA中某些特定基因的改变可能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有关[42]。
肝切除、肝移植和局部治疗(如消融治疗、动脉化疗栓塞、内外放疗和肝动脉灌注化疗)已被广泛应用于HCC的治疗[28, 43]。尽管如此,5年内HCC患者的术后复发率仍保持在>60%的高水平[44],相当多的术后患者可能有隐匿性微转移或MRD,而没有临床或影像学迹象。然而,ctDNA可以作为检测MRD的生物标志物。值得说明的是,MRD是指癌症在治疗后体内持续存在的低于常规检测标准的残留在体内的少量癌细胞。这部分癌细胞多属于对治疗无反应或耐药的癌细胞,一般不会引起任何症状或体征,且不能被传统影像学(包括PET/CT)或实验室检查方法发现。并且研究[45]表明,MRD的存在与复发风险增加和较短的生存期有关。如今,MRD检测技术已被应用于部分血液系统疾病中(如急性髓性白血病)[46]。Cai等[26]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术后ctDNA阳性患者被认为是早期复发或转移的高危风险因素,说明ctDNA可以作为监测HCC中MRD的可靠生物标志物。其结果还显示,ctDNA与蛋白质生物标志物脱-γ-羧基凝血酶原的结合提高HCC患者MRD评估的敏感度,这将有利于更好的指导术后治疗的临床决策。另一项研究[4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者鉴定了4种热点突变(TP53-rs28934572、TRET-rs1242535815、CTNNB1-rs121913412和CTNNB1-rs121913401),结果表明ctDNA中特定的突变可定义为H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ctDNA可以实时监测不同突变体的纵向变化和治疗反应。例如,Cai等[25]报道了1例患有体细胞突变(HCKp.V174M)的患者,这种改变在第1次TACE治疗后被发现,然后在第2次肝脏手术后变得无法检测到,并在第2次复发时急剧增加。总之,与传统的影像学检查和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不同,跟踪ctDNA的体细胞突变频率能够实时监测肿瘤负荷和评估预后结果。
尽管ctDNA作为用于无症状个体和残留疾病的癌症检测的新型液体活检标志物已获得相当大的关注,但要实施于临床工作中仍存在许多挑战。由于ctDNA从癌细胞中释放出来,其携带肿瘤特异性遗传信息或表观遗传变化,这些信息在正常cfDNA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准确检测和区分有效的ctDNA与正常cfDNA非常重要。同时血浆中的ctDNA主要来源于肿瘤细胞的破裂和释放,血浆ctDNA的浓度会受到不同生理和病理条件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增加ctDNA的降解或白细胞裂解产生的细胞基因组DNA的污染[48]。所以,如何保证ctDNA是癌症特异性来源并不含有其他杂质的,这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问题[37]。还有研究[49]已经证明,造血细胞具有非恶性突变的克隆造血。这就模糊了cfDNA是来自外周血细胞的破裂还是造血细胞的克隆性造血,造成基于特定cfDNA基因分型指导癌症治疗的准确性降低。事实上,人们一致认为通过使用细胞稳定管并避免重复冻融循环进行特殊处理可以提高ctDNA的产量和纯度,但是不同的ctDNA纯化方法和各种修改方案都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其次,与患者相关的因素(如医疗、吸烟、运动、与年龄相关的克隆性造血、炎症或心肺疾病等),也有助于ctDNA的释放[11]。此外,临床医生迫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敏感度和特异度的通用工具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尽管ctDNA的突变及其甲基化模式作为MRD的检测已成功应用于晚期常见癌症,但15%的转移性癌症患者可能没有足够的ctDNA水平来进行血浆突变分析[50]。另外,HCC患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和普遍可行的突变,导致基于HCC相关基因突变的血浆中基于ctDNA的MRD检测的医学应用很少。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开发了许多用于ctDNA基因分型的检测技术(如ddPCR、NGS、MFC等)。然而,每种技术的测试特征各不相同,并且适用于不同检测下限的不同患者群体。因此,若要直接比较各种技术的高诊断特异度与适度敏感度,需要严格的交叉分析比较。ctDNA检测对癌症的低诊断敏感度可能是导致组织和ctDNA基因分型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51]。
根据系统生物学的观点,基因组代表的是一种潜能,其经转录和翻译之后所形成的基因产物——蛋白质是机体生物学行为的最终“执行者”,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和治疗直接相关。而且,蛋白质的表达并不完全依从于基因组:一方面基因组水平检测到的突变在翻译阶段可能会存在沉默表达,最终并没有执行实际生物学功能;另一方面许多癌症的发生可能起源于蛋白质整个翻译过程的调控阶段,而仅基于DNA层面的突变检测难以确定其与肿瘤发生的相关性。此外,遗传信息从DNA传递到蛋白质的过程中存在级联放大现象,一个DNA分子由多个碱基对组成,因碱基对突变的多样性,故产生的蛋白质同样具有多种性,此处包含了转录、非编码调控、翻译效率、蛋白修饰等的影响,也包含与该蛋白相互作用或者同一信号通路的相关分子的改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肿瘤的周围环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该改变甚至会早于肿瘤发生,机体的免疫监测及反应在不同患者之间甚至在不同癌症之间可能不尽相同。由于该步骤不涉及核酸序列水平变化,常规的DNA检测无法企及。通过蛋白(或蛋白多组学)进行肿瘤特征分子发现,可以进一步过滤假阳性的可能。
在精准个体化治疗的时代,ctDNA检测技术改变了肿瘤的诊断方式和治疗方案,因其可应用于肿瘤的早期诊断、预后判断、疗效检测及复发预警等多个方面,从而为临床工作带来了新的决策思路。但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点、检测方法和技术的限制,应用于临床实践仍有较大难度。考虑市场应用前景、产品研发进程及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关键位置,基于蛋白的检测技术有必要尝试,且值得期待。
侯志远, 刘源, 杨超然, 等. 循环肿瘤DNA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2, 38(11): 2616-2620.
查看更多